北京,长安街上,北京音乐厅。
1024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全中国最挑剔的音乐爱好者在这儿,以往都是来欣赏大师的。
这一天,面对台上一群最小9岁、最大也不过16岁的孩子们,他们的情绪在12分钟内,由平静到流泪,由流泪到激动不已地鼓掌。
突然,台上响起一句话,掌声猛地收住了。

替代掌声的,是每个人把四指收拢在掌心,将大拇指竖起来,这是人类掌握的最简单的一种手势。
而观众们齐刷刷地比出它,是因为刚刚12分钟里,用歌声带来震撼和惊艳的这14个孩子,听不见掌声,说不出话。
没错,他们是大家口中的“聋哑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的传承人蔡雅艺为他们伴奏,窦唯的制作人丁漫江专程录音,蒋雯丽等无偿录制VCR。
所有光环和名头到了14个孩子面前,都成了配角。
这一切,是5年前被骂作神经病的李博和张咏,怎么也想不到的。
被一嗓子推到山里
5年前,广西百色凌云县一间特殊学校里,突然来了两个奇奇怪怪的人。
你会发出“啊”的声音吗?他们见人就问。
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们,怯怯地用手指比划了一下——我不会。
从聋一班到聋四班,问遍所有人,得到的都是否定,两个怪人崩溃了。

怪人一号,北京艺术家李博,年少成名,一幅画卖到百万,法国的皮尔·卡丹艺术中心称赞他是国外最佳艺术家。
怪人二号,厦门音乐人张咏,摇滚乐曾是他的骨和血,live现场让小年轻们都疯了。
原本两个人要在不同领域走下去,拐点出现了。

那是北京街头,人声鼎沸,突然响起一声呐喊,这是什么声音?见惯了好艺术的两个人,竟然闻所未闻——那么干净、纯粹,好像把整个生命都放在里面。
急忙去寻,却发现声音的源头,原来是一个聋哑人。
这一嗓子刷新了二人的世界观,他们决定去聋哑学校里搞点这样的“呐喊”放进音乐里,也震震其他没听过的人。
亲朋好友都无语了,用聋哑人的声音采样,你们是不是神经病?

沉浸在自己世界的聋哑孩子
两个人没搭理,那声呐喊给了他们信心。成年人都做得到,更何况是更纯粹的小孩子?
没想到,山中生活并没有让一切简单起来。这里长大的孩子们,同样要承受冷眼、嘲笑。
一扇简陋的校门,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也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

借助手语翻译,李博和张咏用尽一切办法表达:你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多好听吗?你们想发出声音吗?
摇头,还是摇头。两个星期里,两个人像是朝空谷喊话,没得到一声回音。
从校长室出来,两个人被挫败感笼罩,都不说话,准备回房间收拾行李。
就在这时候,一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哒哒哒跑过来,才四岁的小不点儿,仰着头拉住李博,眼神专注,张开嘴——“啊——”。

好听疯了!不仅仅是好听,“她肯发声,说明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影响了。”
此时再走,等于告诉他们,大人会说谎,希望不存在。
他们决定成立合唱团,而那个自信又勇敢的小姑娘,后来,成了无声合唱团中最小的成员——杨微微。

从无声到合唱
有了第一个成员,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然而,把初具规模的合唱团聚在一起,进行第一次训练时,两个人感到深深的无力。
此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起训练聋哑人成为合唱团的先例,全球3.9亿聋哑人,没有一个人会合唱。
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借鉴。任何一次尝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怎么感觉到声音的存在?怎么发出某个声音?怎么发出正确的音高?怎么合唱?
无数道难题摆在面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死结一一破开。

将脸贴在板材上,手指叩击,感受到板材的微微晃动。

用手感受到伙伴发声时,腹部的震动。
凡震动处,皆有声音。这是他们感受声音的独特方式。

我们的舌头卷曲伸直,抵住上颚或牙齿,一个个不同的音就发出来了。通过耳朵的反馈,我们不停调整,渐渐地学会了说话。
但怎么让这些孩子体会到音和音之间的不同?
两个人愁白了头,任是通过手语翻译怎么比划,孩子们还是一脸茫然。
突然,一个小孩嘴里含着的雪糕棍给了他们灵感。
从此,李博就在村里的小卖部打起了“游击”……每天买点雪糕,再带点棍子,借助雪糕棍和舌头的配合,孩子们知道了啊、哦、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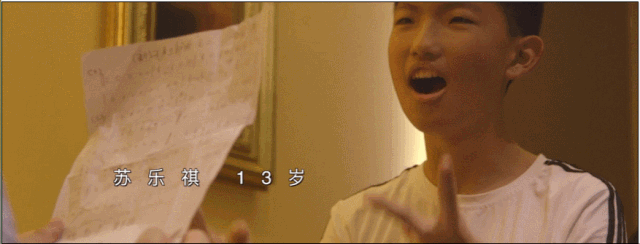
土方法用尽后,张咏和李博开始告诉孩子们,你是女高音、你是男低音……
为了发出标准的音高,他们第一次动用了一个专业玩意儿——校音器。手还很小的杨微微,拿着校音器,一边张嘴发出声音,一边观察着指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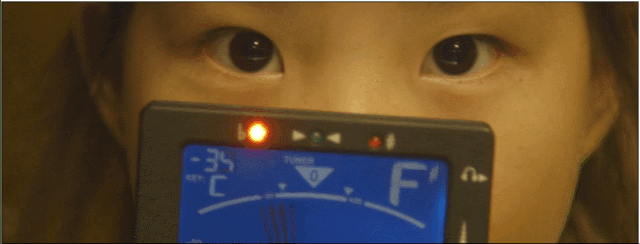
当指针指向某个数字,他们就知道了,这个音高是属于自己的。而从用校音器知道,到记住这个音高,中间要经过无数次练习。

为了让声音更稳定,每一个孩子,每天都要背部紧紧靠着墙面,踮起脚,感受那个玄乎的、叫丹田的东西。

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他们过了五年。


五年里,世界快速迭代。
唯一不变的,是李博和张咏每年像候鸟一样,去广西的山里几个月,和孩子们闭关。
李博的画廊关了,张咏的live演出中止。靠着以前那点“家底”,两个人在坚持。
也不是没想过借助基金会来做事,但是发现有些满嘴跑火车的所谓基金会其实就是想利用孩子们在北京音乐厅赚上一笔的时候,他们果断选择解约。
一时间,初具雏形的合唱团,接近停摆。

没有基金会就做不成事吗?两个人不信这个邪。于是,在朋友刘二喜的描述里,他们:
“如家住不起,那就睡在北六环外一个度假村的员工宿舍;
外卖吃不起,就蹭人家的员工食堂;
大巴坐不起,就找朋友借车,自己当司机;
连吃上三个月的6元老友粉早午餐;
以及最后半个月每天只睡4个小时……”
48小时里,两人轮流开车,从广西一路行驶2700公里,抵达北京——长安街——北京音乐厅。孩子们兴奋又紧张。

5年的时间漫漫,
终于要凝结出舞台上的12分钟。

闪光的12分钟
一开始,南音的传承人蔡雅艺用洞箫吹出第一个音,王咏的手在他们申请了国家专利的独创乐器chén上,蓄势待发。

孩子们穿着白色T恤,双手背后,看上去,也没有一般合唱团的样子。观众们有的双手抱胸,有点戒备,有点搞不懂,这是要干嘛?

突然,李博用手语比划了一段,随即拿着指挥棒,身体一压一弹,双手挥动。

面对一千多个人,14个孩子有点“绷住”,手指还在身后小小活动着来缓解紧张。
但李博这个讯号一发出来,五年里练了千百次的孩子们瞬间读懂。
“嗯、啊、哦……”他们如约一个接一个,发出了第一声。
音乐家刘索拉形容这是天外来客的声音。
像是给每天习惯了各种杂音的我们,一声“砰”的撞击。

大鼓急速擂动,比鼓声更激动人心的,是他们的合唱。李博一手划到高处,孩子们的声音也攀登至高点。

随即,这些顶尖音乐人们扭动了起来,整场演出最有趣的部分,来了。

留着小平头的男孩何青东上前一步,手势打起来,自信地开始“叭、叭”唱起了r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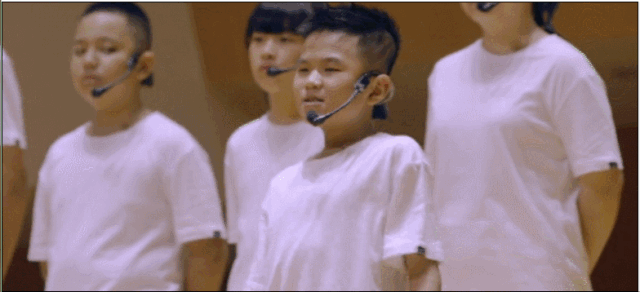
随后,小伙伴加入进来。两个人极有节奏的声音,带动起身后的合唱团成员。

仿佛体会到那种生命本真的喜悦、快活、欣然……台下的观众开始眼睛含笑,晃悠脑袋、打起拍子……

经过“希声”、“嬉戏”,进入合唱的第三章节——希望。像从一条欢快的溪流,百转千回,进入宽阔的大海。

孩子们的声音,如一束温暖的光,带领着观众,感动、流泪…

12分钟结束,震撼和感动经久不息,所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所有观众用大拇指,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无以为谢,所有音乐人和14个孩子,唯有深深鞠躬。

生命中更多美好的一天
发生在今年夏天的这场演出,给无声合唱团带来了关注、鲜花和掌声。
但是一时之间,也有无数声音传过来,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后,他们还能习惯小山村的简单吗?
就像那句话说的,“我能够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

广西百色凌云县
李博和张咏却想说,你们完全想多了。
去一趟北京,他们都要盘算半天——怕住得太差,委屈了孩子,又怕住得太奢华。
你想想他们来北京待24天啊。21天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不安排好了,他们就回不去了,这个就太害人了。(李博)
在他们看来,比音乐更重要的是做人。五年里每一天的点滴相处,他们都言传身教。

所以,经过这五年,孩子们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个发光体。他们已经不需要外面的光来照亮自己。

从北京回来,亲戚村民们对这些曾经被看做“有缺憾”的孩子,也刮目相看。

他们看跟拍的视频时发现,曾经最自卑的孩子在合唱团呆过后,慢慢慢慢,成为了最自信的那一个。

他们一起训练。

一起大笑。

很多人觉得这是李博和王咏对孩子们的公益,他们却觉得,自己被这些孩子改变了,美好的改变。
曾经做的事换来了金钱,但也带给他们迷茫。在孩子身上,他们重新体会到艺术的纯粹,生活的乐趣。
如今有商演找过来,他们通通拒绝。怎么能耽误孩子的学习?

曾经不被所有人看好时,他们说,“谁怎么看我们都没关系,只要心是正的,我们什么都不怕。”

如今聚光灯一下全照过来时,他们却说,“重要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而是他们回去之后,能更好、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北京音乐厅那一天,是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一天。那之后,还有更多更多美好的一天,等待着他们。
去唱出来,去活出来。
让善意催生出更多的善意,让温暖催发出更多温暖。
看到这一张张治愈的笑容,他们做到了。
